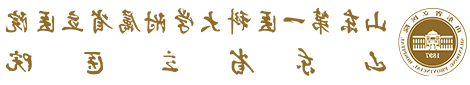医院人文
香附草
香附草
■ 房广星
乡下孩子的童年,似乎总与无数的植物有牵扯不断的联系。就像那些永远存在于童年记忆中的田野,青草,牛羊,露珠,彩虹,星星……
或许,香附这样一种植物,这样一种药物,从我开始学习中药学这个专业开始,开始接触香附这种药物的一刻,我就无法控制地把自己拉回到乡下那个环境里去,拉回到村子南端那道宽阔的水渠边和那些长满了水渠两岸的香附草。
那道水渠有多宽我说不清,只是在儿时的记忆里感觉很宽。水渠在村子的南部,北面是一个很大的果园,我和小伙伴们在秋季果子成熟的时候常常不顾围绕果园的荆棘篱笆,钻进去偷摘苹果或山楂,惹得看园子的老爷爷破口大骂。很多年后,当我再回到老家,凭记忆循“旧路”去寻找这些深深地印在我儿时记忆里的事物时,却总是失望而归的。这些年,眼看着我小时候的村庄不断扩大,不断侵占成片的农田,而盖起房屋,或工厂,然后闲置下来,等待升值。我困惑,也痛心。我特别怀念小时候那大片的田野,怀念那道在村子南部静静存在的水渠,水渠旁的果园,地瓜地……
我对那道水渠的记忆更多地不是停留在果园和地瓜地上,尽管偷果子的童年乐趣让我知道自己曾经的年少,尽管地瓜地里那些高举着的紫色的地瓜花也曾紧紧抓住我少年的目光和心情,还有不时附在地瓜叶子上面绿色或近紫色的豆虫会惹动少年的活力与好奇。但离开故乡好多年后,当那样的少年时光永远不再之后,留存在我记忆里并且更鲜活的,却常常是长满了水渠两岸的香附草。
当然我无法为自己找到一个理由来说明对香附草的特别记忆,也实在没有。香附草本身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一个乡下孩子去记忆之处。这种草严格来说在乡下并不是一种优质的草,甚至可以说是最容易被舍弃的。因为香附作为草类,其地上的叶子粗糙,坚硬,少水分,牲口不喜欢吃,而且在那个年代,打了草要背到生产队去过秤积工分,打这种草质坚硬却又没有份量的香附背到生产队的牲口院里去换工分,绝对是最差选择。特别是香附草因为其地下有根茎,在土地里附着力强,打这种草特别容易把手划破。
但事实是,这些并没有妨碍我对香附草的特殊记忆。
这样的记忆来自于一个少年的独处与遐想。对一个乡下孩子来说,下学后的时光漫长而无聊。那时候没有电视可以看,没有书可以读,除了与伙伴们疯玩,就是背上草筐,到田间地头,打上一筐草,或背回家喂自家的猪羊,或背到生产队的牲口院里“卖”掉,帮家里的大人们挣几个工分,等到秋后的时候多分几斤粮食,好应付一整个冬天和春天的饥饿。我喜欢一个人来到这道水渠边,不是为了打草,而是为了一个人坐在长满了香附草的渠岸上,手捋一把香附的叶子,或拔几根白茅根在嘴里咀嚼。然后,呆呆地看着水渠对岸的田野,或在田野里忙碌的乡亲们。或者干脆躺在香附草上,根本不顾坚硬的叶子刺痛了皮肤,看蓝蓝的天空,在蓝蓝的天空上闲闲地行走而过的白云……
几十年后,我坐在城市狭小的空间里来回忆这些时,却并不觉得那样的“神游”的无聊和狭隘。相反,我觉得那个少年的自己才真的阔大,真的幸福,真的诗情画意。中年的自己开始无法克制地思念那些下学后闲暇的时光,那些长满了水渠的香附草,及各种植物们散发出来的清香气味。那样的少年时光或许平淡,没有故事,但我想,这些就足够了。
(原载院报2011年6期)